

2021年9月15日20時20分至23時20分,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在Zoom會議室觀看網課“中國宗教文獻”第二講錄像,然後共同討論。
本次課程主題為“早期中國宗教文獻”,主講人為呂鵬志教授。在錄像中,呂教授結合早期中國宗教的三部史志即《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書·祭祀志》講解了先秦至後漢的中國宗教(詳情可參《神州研究》第二期,第23-24頁)。
課程錄像播放完畢後,呂教授和參加課程的同學就本講涉及到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討論主要涉及《史記·封禪書》的文字內容和文獻考訂。
在文字內容方面,本次討論內容集中在《史記·封禪書》相關的疑難字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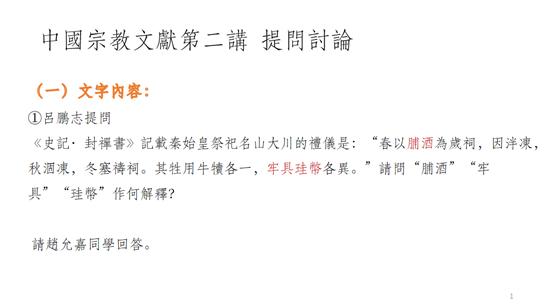
《史記・封禪書》曾記載秦始皇祭祀名山大川的禮儀,其云:“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呂老師就其中“脯酒”、“牢具”、“珪幣”的含義進行了提問。
趙允嘉同學認為以上三種應該都是祭祀時用的祭品。“脯酒”應為肉干和酒,“牢具”是包起來祭祀的牲體,“珪幣”則是“犧牲玉幣”,即牲畜祭品和祭祀用的玉帛。隨後,呂老師就“牢具”一詞的含義與參課老師許詠晴進行了探討。呂老師認為“牢具”應為祭祀用的祭器,或指犧牲祭品和盛放祭品的器具。許老師則根據《禮記·雑記》孔穎達疏(孔穎達疏:“遣車視牢具。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爲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認為“牢”亦可解釋為“牲體”。
《史記・封禪書》對方士李少君的方術有這樣的描述,其曰“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中“使物”、“致物”一詞尤難理解。
廖文麗同學根據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引三國曹魏如淳注:“物,鬼物也。”認為“使物”指控制鬼神,“致物”指招致鬼神。
隨後呂教授提問,《封禪書》中的“使物”、“致物”與《禮記·大學》中的“格物”有何關係?
廖同學在呂教授的提示下,指出《禮記·大學》中的“格物”之“物”亦可訓為“鬼神”。根據牟潤孫的研究(牟潤孫《論格物致知》,《海遺雜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07-314頁),“格”即“至”、“來”,“物”即鬼神,“格物致知”即言神明降附於人,人便有了智慧。如《管子·內業》云:“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閒,謂之鬼神。藏於胷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總之,牟氏的研究證明了《大學》與黃老道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聯繫。
《史記》一書在轉述他書時常用“傳曰”一語,在《封禪書》中亦有一例,其云:“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此文句又見於《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呂教授據此提問,如何理解此處的“傳曰”?
王盛維同學認為“傳曰”中的“傳”有书傳、著作之義,如清趙翼《廿二史禮記·各史例目異同》云:“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此處的“傳”應該是指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薛聰同學補充道,這裡的“傳”確實指的是《論語》。《尚書序》:“至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孔穎達疏:“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然而,司馬遷所處時代已有《論語》之名,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張丞相列傳》:“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既然如此,為何司馬遷在此處不言“《論語》曰”而言“傳曰”?從全書來看,“傳曰”所引之語除《論語》之外,亦有見於《荀子》《禮記》《老子》等書,也有其他出處未知而僅存在於《史記》之中的引文。先秦兩漢文獻在引用他書時,也常用“傳曰”一語(可參康廷山:《先秦子書所引“傳”體文獻來源考辨——兼論“經傳”之“傳”名之源起》,《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40(05):115-120)。由此可知,“傳”並非只是《論語》《孝經》的別稱,而是涵蓋許多書的統稱。東漢劉熙《釋名》云:“傳,傳也,以傳示後人也。”劉勰《文心雕龍·論說》:“傳者轉師。”范文瀾註:“轉師,謂聽受師説,轉之後生也。”司馬遷之所以用“傳曰”,蓋當時《論語》《荀子》《老子》《禮記》之書皆被視為師徒學術傳授所匯集而成的文獻,與具有權威性的六經相對(“六經”最早見於《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姦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所以孔穎達說“傳”非“先王之書”。又東漢王充《論衡·書解》:“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西晋張華《博物志·文籍考》:“聖人制作曰經,賢人著述曰傳。”如此看來,作為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論語》確實屬於“傳”的範疇。總之,司馬遷在《封禪書》中用“傳曰”而不用“《論語》曰”可能是當時該段引文尚未被編入《論語》,而散存於師說文獻之中;亦或當時流行的寫作習慣,即“傳曰”是引用賢者之言或師說文獻的慣用語,猶今人語“有的書說……”“古人曾說……”。另外,《莊子·天下》云:“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篇的作者認為百家之學(方術)都是對六經(道術)的稱道,此亦可證《老子》《荀子》等諸子之書屬於“傳”的範疇。
在文獻考訂方面,參與研討的師生主要圍繞《史記·封禪書》對《尚書》《周官》引用文字進行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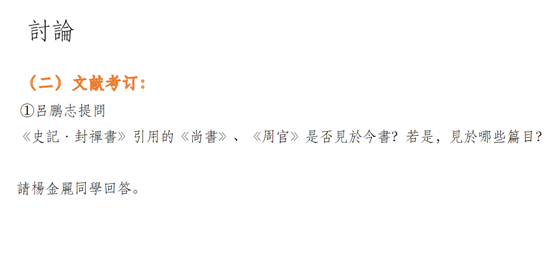
楊金麗同學指出《史記·封禪書》引用《尚書》部分見於今書。具體而言,“尚書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東後。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等引語出自《尚書·舜典》《湯誓》《高宗肜日》《說命上》《咸有一德》等篇章。據顧頡剛等人的考訂,《舜典》先秦時已佚,東晉的偽《古文尚書》將《堯典》的後半部分拆分出來冒充《舜典》,《尚書校釋譯論》一書將其恢復,歸入《堯典》。一般認為《周官》即是《周禮》,而《史記·封禪書》所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不見於今本《周禮》,而是見於《禮記·郊特牲》《禮記·王制》。這說明司馬遷時代的《周禮》與今本還存在區別,當時《周禮》的內容可能要比今本《周禮》更豐富。
《封禪書》中曾記載孔子對封禪、禘、旅等宗教活動的評議。呂老師據此提問,在司馬遷眼中的孔子是否信仰宗教?
張晨坤同學指出《封禪書》中,孔子對封禪、禘、旅這三種宗教祭祀活動的態度記載如下:“其後百有馀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馀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甯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禅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這段話的大意是孔子論述六藝,記載封禪泰山的人,而論述中卻看不到有關封禅的俎豆之禮。司馬遷認為大約是難以記述的緣故。曾有人問及有關禘祭的事,孔子說:“不知道。倘若知道禘祭的事,對天下任何事都如同觀察自己的掌文一樣明白了。”對於魯國季氏旅祭於泰山,孔子也曾譏笑。結合《論語》,從表面上看,孔子是不言宗教與鬼神的,即“子不語,怪力亂神。”但實際上,孔子有很多關於宗教活動的言論。關於《史記·封禪書》中孔子對禘、旅二禮態度的記載,其實可以解釋。第一,禘禮年代久遠,孔子難聞其詳。第二,孔子認為禘、旅這兩種祭祀方式是皇帝的專屬權利,但孔子並不認可季氏的統治地位,因此譏笑。《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由此可見,司馬遷眼中的孔子應該是信仰宗教的,只是文獻的記載比較簡略。
張同學回答完畢後,呂教授對這個問題又進行了補充:首先,禘祭是指天子舉行祭祖典禮,旅祭是指天子祭天下山川。其次,司馬遷記載孔子態度的這段話來源於《論語·八佾》。祭祀泰山是天子和諸侯的專權,季氏是魯國的大夫,孔子認爲他祭祀泰山是“僭禮”行徑。因此,孔子並不是不信仰宗教祭祀,而是他認為當時統治者的祭祀禮儀違反其所推崇的周禮,是不合規矩的。
《封禪書》中記載了西漢以前的宗教活動,其中也包括前代久遠的周代及周以前的宗教活動。呂老師對此提問:《封禪書》關於周代及以前的宗教活動是否真實可信?有無判斷真偽的依據?
廖同學認為《封禪書》中所記載的周代及周以前的宗教活動不太可靠,應該是傳説。《封禪書》顯示商代流行“德”的觀念,而根據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962-964頁),作為道德意義的“德”字,在甲骨文中是沒有的,直到周代金文和文獻中才出現。殷商奴隸主依靠嚴厲的刑罰和上帝的權威進行統治,當時沒有形成也不具備“德”的觀念。當時上帝擁有絕對的權威,一切吉凶都靠上帝意旨。遇事只用考慮是否符合上帝的意旨,而不需要考慮道不道德。他們認為“有命在天”,上帝保障統治,心中根本不存在德的觀念。商朝時擁有絕對權威的“帝”是沒有德的。他們的一切活動都通過占卜來獲取上帝的意旨,在他們的意識中沒有德這樣的概念。道德的德是在西周時出現使用的。如《尚書·周書》“皇天無親,維德是輔。”周朝吸取殷商滅亡的教訓,感到“天命無常”,開始懷疑帝的權威,發現單純依賴上帝的意旨並不可靠,於是加入了“德”。宣稱“以德配天”,以延續自己的統治。但其需要沿用商朝的天命權威,鞏固統治,德的一些外在表現慢慢就形成了禮。許老師對此發表了不同看法,認為甲骨文中已出現“德”字,只不過其含義不是“道德”之“德”。
其次,《封禪書》曾提及“五嶽”一詞。根據《尚書校釋譯論》(第131-134頁),“五嶽”概念在舜帝時代尚未形成,五嶽具備特定的名稱是漢朝才有的事。在堯舜時代,有座山叫四嶽,將其奉為信仰的百姓通過通婚搬遷等將嶽字帶到各處給山命名,但在當時僅是普通山名,沒有特定的神意。而《堯典》作者附會,將四嶽專名變為四嶽通名,加之中央即成為五嶽。實際上,是到漢武帝定東、中、南、北嶽,漢宣帝時定下西嶽,至此五嶽概念才正式形成。在分散未統一的先秦,不可能定下全境內的五嶽。《堯典》作者只是根據神話中以嶽命名的山來拼湊,但對後來五嶽的形成造成了影響。
最後,呂老師總結道,本次課程及研討的目的是為同學們介紹早期中國宗教的基本知識,以便同學們更好地理解早期中國宗教與道教之間的聯繫與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