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禮》研討
2021年9月23日晚上8時20分至11時15分,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師生在Zoom會議室集體觀看由中心開設的“中國宗教文獻”網課第三講,並就此講涉及的課題展開研討。
本講由西南交通大學吳楊老師主持,香港中文大學張曉宇老師主講,主題為“《禮》學簡述暨《儀禮經傳通解》解題——以郊廟時祭中的‘九獻’儀式為例”。在去年的課程錄像中,張老師主要介紹了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文獻以及三禮學的形成與發展,並著重探討了保存在《禮記註疏》中的崔靈恩“九獻”說(詳情可參《神州研究》第二期,第25-26頁)。
在課程錄像放映完畢後,呂教授與張曉宇老師就網課中提到的崔靈恩註引《周禮》“九變而致人鬼”一句進行了探討。呂教授指出,《史記·封禪書》曾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此可證司馬遷所見的材料即出自《周禮·春官·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大司樂》中所提到的數字,如“六變”、“八變”、“九變”非常特別,它們是否與《周易》中的陰陽之數(六、八屬陰,七、九屬陽)存在關聯?
張曉宇老師回答道:關於樂的變化,禮學上有不同的講法。一是認為變數與降神難度相關。人鬼最為複雜,最為難降,所以需要九變,如賈公彥疏云:“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人鬼九變也。”一是認為變數是調和眾樂的結果。鄭玄認為在祭祀中需要遍奏六代之樂,若是致人鬼,則需要六十三變。如此則耗時太長,所以只能有所選擇地演奏。比如在梁武帝時期,就只用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樂。所以,這裡的變數可能是調和後的結果。至於變數是否與《周易》的陰陽之數有無關聯,如果考慮到《周易》的影響,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如崔靈恩(崔曰:“凡樂之變數,皆取所用宫之本數爲終。夾鐘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鐘在未,未數八,故以八變而止;黄鐘在子,子數九,故九變爲終也。”)和清儒江永(江曰:“揚雄《太玄》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即聲律之數也。”)的註解就恐怕受到漢代京房律的影響。
隨後,參加課程的師生對有關三《禮》文獻的文字內容、文獻考訂及其他問題進行了交流和討論。
在文字內容方面,本次討論主要涉及上古祭祀中的祭法和祭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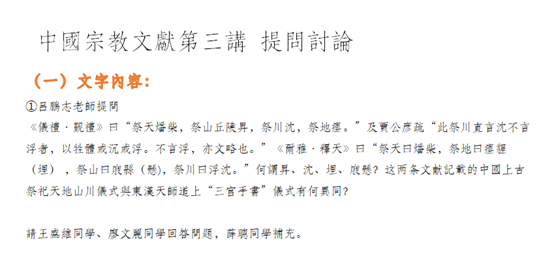
祭祀天地山川是古代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動,但不同的祭祀對象,其祭祀方式有所不同。如《儀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昇,祭川沈,祭地瘞。”《爾雅·釋天》亦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貍(埋) ,祭山曰庪縣(懸),祭川曰浮沈。”呂鵬志教授對其中的儀式術語“昇”、“ 沈”、“ 埋”及“庪懸”進行了提問。
王盛維同學認為“昇”就是祭山之時要把祭品放置於山上,與“庪縣”同義,唐代賈公彥疏云:“昇即庪懸也。”“沈”,亦作“沉”,因向水中投祭品,故得名曰“沉”。“埋”,即埋物祭地,是古代祭地的祭法。對於《爾雅》中的“祭川曰浮沈”,廖文麗同學引用賈公彥疏補充道:“此祭川直言沈不言浮者,以牲體或沈或浮,不言浮,亦文略也。”對於“庪縣”,薛聰同學在此補充了兩種解釋。東漢李巡云:“祭山以黄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遥遥而眂之若縣,故曰庪縣”;曹魏孫炎云:“庪縣,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根據清儒鄭珍在《說文新附考》中的評述,李說是以將“庋”解“庪”,孫說則是以“跂”解“庪”。若從《儀禮》“祭山丘陵昇”來看,李說似乎合理。張曉宇老師則認為,就《爾雅》內部系統而言,孫說能夠圓通,但不一定代表當時的實踐情況。“庪縣”一詞實難判斷是非,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同學們在閱讀三《禮》的過程中,如遇到這類疑難問題,除了參考漢唐註疏外,可以多多閱讀清人的相關著作。其中,有四本書非常值得閱讀。一是秦蕙田的《五禮通考》,此書乃禮學資料集的頂峰之作。二是黃以周的《禮書通故》,此書問題意識較為突出。三是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此書是傳統註疏章句之學的頂峰。如涉及到禮學上一些條例性、規則性的問題,則要參考凌廷堪的《禮經釋例》。若熟讀這幾部書,基本能解決大部分的禮學問題。
呂鵬志教授進一步提問,《儀禮·覲禮》《爾雅·釋天》所記載的上古祭祀天地山川的儀式與東漢天師道的“上三官手書”(《三國志·張魯傳》註引曹魏魚豢《典略》曰:“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有何異同?
廖文麗同學回答道:從祭祀所傳達的地點來看,東漢天師道的“上三官手書”是將三通文書分別置於山上、埋於地中、沉入水底,以上呈天官、地官、水官,故稱為“三官手書”。這與《儀禮·覲禮》中的“祭山丘陵昇,祭川沈,祭地瘞”及《周禮·春官·大宗伯》中的“以貍沈祭山林川澤”頗為相似,故“上三官手書”當是東漢天師道對上古祭祀儀式的承襲。但同時二者也有不同之處。根據呂教授的提示,主要有兩方面的差異。從祭祀對象來看,上古祭祀儀式要祭祀天、地、山、川等神靈,而東漢天師道的“上三官手書”只祭祀天官、地官、水官,在祭祀對象上有所縮減。從祭祀物品來看,上古祭祀是血肉殺生之祭,雖也有祝詞一類的文書,但免不了供奉犧牲玉帛等物品。而東漢天師道則反對傳統祭祀,崇尚與鬼神進行書面交流。總之,正如呂教授在《唐前道教儀式史綱》中所說:“上三官手書對上古祭祀傳統是既有因襲,又有變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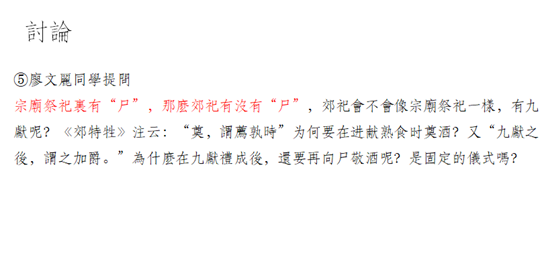
“尸”在古代宗廟祭祀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禮記·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從內涵來看,“尸”即代受祭的活人,象徵著所祭祀的祖先。《儀禮•士虞禮》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廖文麗同學據此提問:既然宗廟祭祀有尸,那麼郊祀是否立尸?
張曉宇老師回答道:宗廟祭祀里有尸是常態,至於郊祀中有沒有尸,禮學上尚存爭議。朱熹就認為郊祀無尸,因為“尸”是神靈的憑藉,若使高貴的天神降臨到人身上,反而是對天神的褻瀆,出於對天神的尊重,當不敢為天神立尸。在實踐中,宋以後亦無此祭法。但是,在早期文獻還是能見到郊祀有尸的記載。如《國語·晉語》:“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為尸。”所以,到了清代還是有學者認為郊祀有尸。但這裡的“尸”並非為天神所憑藉,而是先祖所憑藉的靈媒,因為祭天需要祖先相配。呂教授補充道:《史記·封禪書》引《周官》云:“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看來,“尸”確實只用於祭祖。另外,從宗教類別來看,至高無上的天神降於人身上,乃“巫教”之特徵,與儒教有別。張老師非常認同呂教授的觀點,根據《國語·楚語》“絕地天通”的故事,最初的天地相通,是神通過降臨在巫身上而實現的。但如果在具有理性主義的儒家禮儀中,認為郊天有尸的話,會讓人誤解此時還是天地相通的蒙昧狀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後世禮學家大多強調“祭天無尸”。
“玄酒”是古代祭祀中非常重要的祭品。在課程錄像中,張老師亦對玄酒有過精彩的講解。如崔靈恩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郁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張老師認為“明水鬱鬯”不通,《禮記·郊特牲》孔穎達疏:“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又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故阮刻本“明水鬱鬯”,當據宋紹熙三年(1192)兩浙東路刻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永樂大典》卷3583作“明水玄酒”。至於“玄酒”的含義,唐代註疏對此有過專門解釋。《禮記·禮運》孔穎達疏:“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周禮·秋官·司烜氏》賈公彥疏:“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别,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薛聰同學據此提問:孔、賈二說是否有矛盾?玄酒與明水又有何關係?
張老師認為玄酒就是明水,孔疏與賈疏並無衝突。其實賈公彥在《儀禮·士昏禮》中講得非常清楚,其云:“禮有玄酒、涗水、明水,三者各逐事物生。名玄酒,據色而言,涗水據新取爲號,其實一也。……相對,玄酒與明水別。通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彼配鬱鬯五齊,是明水,名爲玄酒也,以其俱是水,故通言水也。”總之,明水就是主人用盤子在月下所收集的水,主人進一步清潔之後就轉化為玄酒,其本質就是水,所以玄酒就是明水。因為太古無酒,古代祭祀尚用“玄酒”乃一種“尊古主義”的表現。關於玄酒的詳細論述可參考日本學者江川式部的相關論文。在課後,呂教授補充道,“玄”可訓為“天”,《釋名·釋天》:“天,又謂之玄”。“玄酒”亦可理解為“天酒”,所謂“天酒”乃自然之酒,即淡而無味的“水”。又根據徐鵬飛(Gilles Boileau)的研究,淡而無味的“玄酒”、“大羹”恰恰與《老子》中“味無味”、“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無味也”所體現的素樸哲學相互呼應(參Gilles Boileau, “The Sage Unbound: Ritual Metaphors in the Daode jing,”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2013.5: 1-56)。如《禮記·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樂記》:“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老子其實並不反對禮,他主張的是返璞歸真、同於大道的禮。薛聰同學非常認同這個觀點,他認為“玄酒”之“玄”亦可理解為“遠古”之義,如《莊子·天地》云:“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唐成玄英疏:“玄,遠也。”上文引孔疏言“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亦可證。另外,在《老子》的註疏中亦有註家將老子哲學與“玄酒”相聯繫。如唐代陸希聲在注釋《老子》第三十八章“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一段,曾言:“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乎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筦簞之安而藁秸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如此看來,玄酒之“玄”義兼有三:“天然之酒”、“黑色之酒”、“遠古之酒”,三者相互關聯,如《周易·文言》:“天玄地黃”。總之,“玄酒”貴質,與老子之“返璞歸真”的思想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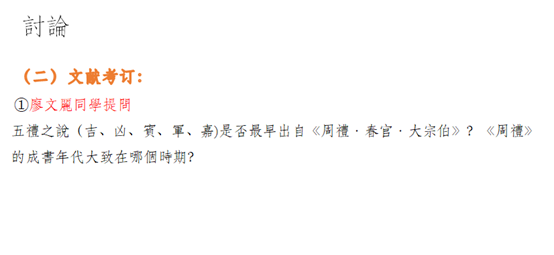
在文獻考訂方面,本次討論涉及《周禮》這部文獻。上周課程我們談及《史記·封禪書》曾引用《周官》,但其引用的內容卻未曾見於今本《周禮》,而是見於今本《禮記·郊特牲》。楊金麗同學認為,司馬遷所見《周官》並非今本,當時的《周官》可能既包含今本的《周禮》,也包括了一些見於今本《禮記》的內容。《封禪書》曾引用《尚書·舜典》云舜“修五禮”,而“五禮之說”(吉、凶、賓、軍、嘉)亦見於《周禮·春官·大宗伯》,廖文麗據此提問,“五禮之說”(吉、凶、賓、軍、嘉)是否最早出自《周禮》?《周禮》的成書年代大致在哪個時期?
張老師回答道:關於《周禮》的成書時期主要有三種看法,一是《周禮》由周公所作,二是《周禮》成書戰國,三是《周禮》成書於兩漢。錢穆認為《周禮》絕不是周代之書,因為《孟子》以前的文獻並未引用。金春峰認為《周禮》中保存了許多秦代禮制。張老師比較傾向於“層累說”,即《周禮》的成書有一個漫長的層累過程。至於“五禮”一詞最早見於《尚書·舜典》,但說“五禮”是“吉、凶、賓、軍、嘉”則是孔安國的《傳》,孔安國是西漢人,故“五禮之說”不會早於西漢,更何況孔安國《傳》是魏晉人的偽作,並不可信。因此,就目前來看,“五禮之說”(吉、凶、賓、軍、嘉)的文獻源頭確實是《周禮·春官·大宗伯》,另一方面,“吉、凶、賓、軍、嘉”五禮作為朝廷禮制則見於西晉的《新禮》,其內容與《周禮》相似,但此書很早亡佚,而自此以後,朝廷禮制皆用五禮。因此,就“吉、凶、賓、軍、嘉”的實踐源頭可以追溯到西晉。呂教授補充道,司馬遷在《封禪書》中引用《尚書·舜典》僅提及“五禮”一詞,並未言“吉、凶、賓、軍、嘉”,這說明司馬遷的時代已有“五禮”之說。
本次課程,參與課程的師生亦對其他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作為三《禮》之一的《禮記》,由西漢戴圣所編,稱為《小戴禮記》。但此書各篇成書時間和材料來源並不一致,故各篇行文風格不盡相同。《禮記·曲禮上》云:“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其中“禮不下庶人”鄭玄註:“爲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註云:“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薛聰同學認為若依鄭註,“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與上下文似無關聯。
張老師認為“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為一節,主要講述相見禮,“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則主要講軍禮。以此來看,上下文確實沒有關聯,其原因在於《曲禮》本身的體例。《曲禮》大概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沈文倬先生認為主要作者是曾子及其弟子,其所記載的是曲微的古禮。《曲禮》的內容大致是由不同的簡牘拼湊起來的,但是並非無序的拼湊,鄭玄《三禮目錄》:“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換言之,《曲禮》是按照“吉、凶、賓、軍、嘉”的總則進行編輯的。所以看起來《曲禮》有些地方雜亂無章,其實是有其編輯原則的,這是《曲禮》與其他篇章的不同之處。
討論環節結束後,呂教授對張曉宇老師的耐心講解表示了感謝,並向同學們分享了他對本次課程研討會的三點總結:一是三禮向來難治,所以同學們需要學會閱讀前人的註疏。二是禮學中的許多疑難問題,我們不僅要參考漢唐註疏,也要注意參考宋人、清人的註疏。三是在研究相關禮學問題時,亦可運用經史互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