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葉明生先生纂《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
李唯希**
閭山教是起源於我國南方的民間道派。閭山教淵源駁雜,內涵豐富。它源於閩越巫法,宋末以来與瑜伽教結合,又與流播於民間的正一道法相融合,至今活躍於民間。閩西南地區的閭山教歷史悠久、傳統深厚,而福建省漳平的永福鎮又是閩西南龍巖、漳平、華安、安溪等地眾多閭山教道壇的傳度中心。該書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即為二十多個核心科儀項目的永福建旛傳度儀式形態。
閭山教研究自上世紀70年代,以國內臺灣劉萬枝先生、國外法國勞格文、施舟人教授為肇始,晚學接踵其後,直至90年代,閭山教研究才逐漸引起海內外學者的興趣和重視。葉明生老師就是90年代始較早接觸閭山教的學者之一。經過幾代中外學人近50年勤奮耕耘,閭山教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但也存在不足。首先,早期的閭山教研究缺乏點面結合的精神,田野調查範圍不夠深入,加之相關文獻較少,對閭山教的把握不夠到位;其次,早期研究對閭山教教派整體源流考證、儀式活动搜集研究多,個案研究少;最後,目前的閭山教研究缺少“抓主要矛盾”的問題意識,未能以一系列緊密聯系的問題灌註研究中,存在“輕線索”之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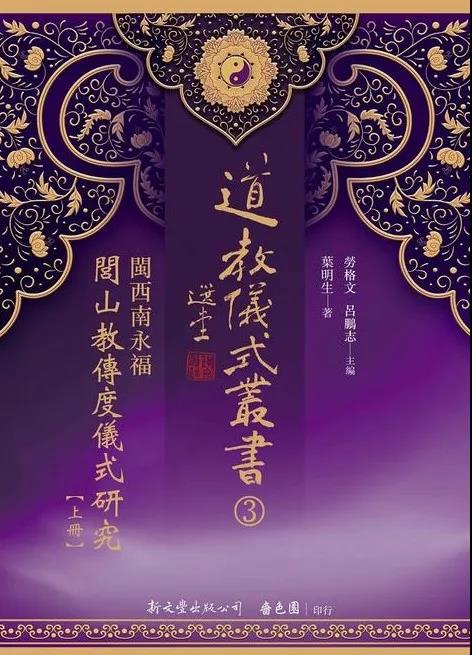
然而此種狀態於90年代後期由於福建省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葉明生教授的努力而得到根本的改變,由他編著並在臺灣新文豐出版的《福建省龍岩東肖閭山教科儀本彙編》《福建省建陽市閭山教科儀本彙編》《福建省壽寧縣閭梨園教科儀本彙編》三種大部頭之作,已開啟閭山教文獻與田野調查全方位研究的大門,取得豐碩成果,在海內外產生很大影響。至於他所著的《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是葉明生教授研究閭山教的新視點,他是以閭山教傳度儀式的核心科儀的角度,來開展對當地道派科法主要表現形式的研究。是針對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這一個案的系統研究成果。該書首次對永福閭山教的教派源流、道壇結構、科儀形態和等方面作出全面論述,並對其教派科法特徵、當代價值和其中的古代宗教信息進行系統解讀,彌補了閭山教研究、民間道教科儀研究的諸多不足。在閭山教研究中,該書具有自己的特色。
筆者通過研讀此書初識閭山教研究,領略了作為民間道教的重要組成部分——閭山教之美。掩卷之余,若有所思,故以牛犢之勇,不揣淺陋,將該書特點臚列如下:
一、田野調查詳實、生動
該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漳平永福閭山教建旛傳度儀式研究,下編為漳平永福閭山教道壇科儀本選編,是上編的拓展資料。作為道教儀式叢書的一個組成部分,該書總體采用民族誌的方法進行研究,輔以歷史文獻法。上編是該書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從人文生態、道壇情況、相關問題研討等幾方面對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進行研究,全面呈現了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是閭山教研究的標誌性力作。
民族誌研究方法,自然以深入的田野調查為基礎。該書的第一章到第六章,皆為田野調查的成果。作者以漳平永福為中心,覆蓋龍巖、漳平、華安、南靖、安溪五縣進行了多次田野調查,並結合1984年到1991年對龍巖城門鄉“道士戲”的調查和上杭“傀儡戲”調查中取得大量的閭山教道壇相關材料,將永福閭山教為中心的傳度覆蓋地區及相關民俗作為一個系統的整體納入自己的視野。在針對永福閭山教的走訪中,作者从1993年至2013年之二十年间多次對當地所有道壇進行調查,並兩次全面參與跟蹤1987年李姓噓靈居和2011年陳姓顯靈壇的傳度儀式,廣泛而深入地搜集材料,對相關的地方人文生態、道壇源流、壇班道士、道壇科儀、道壇結構、道壇法器、道壇法服、道壇音樂及道壇抄本等八方面進行詳細記錄,描繪出福建漳平永福閭山教道壇龐雜的歷史概貌。
在民間道教研究和道教儀式研究中,田野調查論文不少,但能如此詳實、生動的記錄實屬少見。詳實,體現在作者長期深入地接觸永福道壇家族,並善於利用田野材料。許多田野調查僅依靠研究人員數次旁觀、訪談研究對象來獲得田野材料。與此不同的是,作者數年來多次往返永福村,與永福紫陽村顯靈道壇的道師陳金嵐結成莫逆之交,深入參與永福道壇家族生活。族群和道壇關系密切,與族人建立親密關系大大加深了作者對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的理解。該書作者葉明生教授憑借自身多年深入田野的研究基礎,將這些來之不易的田野資料與傳統史學文獻研究法有機結合。中國的宗教、歷史研究有著文獻傳統。對於田野調查得來的資料,常抱著“輕視”的態度,作為用以印證文獻的“輔助品”。《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一書打破這種固有模式,采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經典的“三角驗證”法,使多人口述材料和文獻材料交叉驗證,以獲得某問題視角更加完整的解答。在第三章第一節“永福傳度源始”的分析中,顯靈壇陳金嵐先生、永福當地民俗學家陳仕驥先生的口述及《泉州道教》一書的相關內容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並不一致。作者並不預設先見,沒有替讀者選出答案,而是將結果一並列出,供讀者拓展視野。這種“沈浸式”的田野調查,和將田野材料與文獻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僅為該書提供了詳實的論據,也為閭山教儀式研究乃至整個宗教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為全書嚴謹的架構和深入的分析奠定基礎。
生動,體現在《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一書提供了永福道壇傳度儀式豐富的圖片資料,將內容形成表格,可讀性極強。田野調查中,待研究人員錄音整理的口述材料繁多,待觀察記錄的場景更是數不勝數,要為它們配上圖片,對大部頭著作來說需要耗費作者巨大的心力。然而,民間宗教田野調查所涉及的法器、服飾科儀場景等都在日常生活中難得一見,附上圖片可以極大加深讀者對所述內容的直觀感受。該書總計提供圖片資料204張,對所述幾乎每一個重要物件配有圖像資料,正文中出現的較為重要的符箓文疏也都有一手文獻的掃描件;另提供表格十余張,包括家族族譜、傳度師名單(法名、壇號、年齡、地址等信息)。通過圖片和表格等豐富的形式,讀者的閱讀體驗的同時,也把生動的民間儀式呈現在讀者面前,立體地描述了民間道壇的樣貌。這種詳實、生動的記錄,為將來的地方儀式研究提供了藍本。
二、以儀式為中心進行研究
當前閭山教的種種研究,或拘於某一區域,或囿於某一教派,少見以某種具體儀式為中心。然而,儀式本身正是民間宗教最重要的存在形態之一。如何更加系統地把握閭山教儀式及其意義?如何對共同構成閭山教系統的背景、源流及一系列重要問題作出較高水準的系統解讀和整體研究?這對推進閭山教系統化深入發展又重要意義。該書抓住上述主要矛盾,以永福道壇傳度儀式為中心,對閭山教整體進行有重點的研究。
通過某種具體儀式來把握其道派,可以讓研究者和讀者對其有更直觀、全面的感受,從而更好地為道派定性。基於上述詳實、生動的田野調查和文獻爬梳,作者對閭山教傳度儀式有了更加全面、直觀的了解,從而能夠給出閭山教及閭山教傳度儀式更加科學、準確的概念定義。作者將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定性為“地方家族道壇世襲性的制度化的傳度”。正如該書第五章所描述的那樣,這些科儀不僅是典型的道壇傳度科儀,也是永福當地道派科法的主要表現形式。研究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傳度儀式作為永福閭山教最重要、最特殊的儀式,儀式元素背後的意義覆蓋了整體閭山教教法,對其進行研究可以加深學界對閭山教的認識。其次,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體現了閭山派巫法和道教天師道的科法形態,從中可以管窺歷史上這一地區巫道融合,對認識民間道教的形成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作者從兩方面切入儀式對閭山教進行研究:第一是以儀式意義分析和歷史梳理,勾連永福閭山教整體形態和脈絡;第二是以整體呈現閭山科法的思路搜集科本。
通過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作者綱舉目張地串聯起上篇的七章內容。儀式記錄的主體部分,詳錄了永福陳姓道壇的兩次傳度儀式。以“陳氏道壇”的家族史串聯起第一章“永福當地生態環境”、第二章“永福當地道壇概況”中陳、李、張、鄧、蔡、呂六姓道壇情況;以“傳度儀式”的規制、壇場設施、醮儀及科儀文本勾連起第三章“永福建旛傳度規制”、第四章“永福傳度壇場設施”、第六“永福道壇秘笈”,最後以第七章“永福傳度相關問題研討”整理全文線索,發現並解決問題。這種以儀式為中心的架構,實際上也梳理了永福地方道壇的源流和特色,同時對閭山派的歷史、永福閭山教和其他道派的交互及其現狀進行了分析,點面結合,得出了諸多結論。
在儀式記錄上,作者詳略得當。該書第五章“永福傳度醮儀概述”為全書主體部分,以時間順序記錄了建旛傳度儀式,過程持續數天。對傳度師而言,傳度儀式甚至比婚禮還要重要。傳度儀式的科儀項目有數十個,除去重復的部分尚有二十多個形式、內容相異的項目,全部描述難免主次失衡。作者抓住重點,描繪了其中“開戒壇”“藏身”“裝王身”“造橋造鞭”“發兵入寮”“賞軍”“造牢獄”等重要儀式,使讀者能夠總覽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的概貌。道教儀式繁復多變,尤其是民間道派道、法、釋混雜,即使專家學者也難以把握所有內容。考慮到這一點,作者在對科儀進行描述的時候對各種名詞進行解釋,如“開戒壇”“藏身”“存變”“發兵”“入寮”“請佛”等詞進行解釋,並結合科儀本文本內容選段,和道壇梳理這些儀式或說法的來源。在第二章第四節中,作者就梳理了“請佛”一詞的由來,以口述傳說、莆田傀儡戲《北斗戲》和閭山教神圖《百花橋送子》等田野材料說明了“仁宗禁巫”之事。在這次事件中閭山教為躲避宋仁宗禁巫而把“神”改稱為“佛”,反映了歷史上閭山教的一個艱難時期。永福閭山道壇傳度儀式是當地道派科法的核心,通過解讀和梳理核心內容的關鍵科法和詞匯的意義及歷史,一張永福閭山教的系統之網全面鋪開,為最後一章的相關問題研究奠定基礎。
幾年間“沉浸式”的田野調查讓作者獲得了豐富的田野資料,包括族譜、書影、儀式場面照片,還有當地道壇相關齋儀、符咒文書等。作者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以呈現整體閭山科法整體的思路選用科本,用它們展現了永福當地閭山教道壇甚至閭山教法的宗教形態。如第六章“永福道壇秘笈收錄”中,除了收錄永福道壇建旛傳度相關科書外,還收錄各類閭山教法科本,包括《治邪科全集下大符全集》《治小二廿四癥風全本》等,另有道壇文檢疏式九冊。這些材料多因為其並非直接記錄科法而在過去的研究中被忽略。其實,這些科本通過文字,以復雜的形式傳達了豐富的民俗內涵,折射出作者對民間信仰、社會變遷的認識和理解,是了解漳平永福甚至閩西南地區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不可缺少的材料。
三、問題意識強烈
作為一本研究型著作,該書有極為強烈的問題意識。該書對漳平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的規制及其相關問題進行全方位研究。這麽一部巨著,如果缺乏提綱挈領的問題意識,那麽全書易於散亂無序。所幸的是,作者在開篇前言部分就提出了該書試圖解答的首要問題: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為什麽和別的道教傳度儀式不同,既是具有封閉性的世襲儀式,又是開放性的社區傳度儀式?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作者繼續提出了一些有待研究解答的具體問題,包括為何以“道教閭山派”定名、永福閭山教傳度有何特征、永福道壇中的“陽平治”和“五靈教”提供了什麽信息等。主線問題貫穿全書的材料獲取和相關問題研討,小問題環環相扣推動思路向前,共同建構起該書縝密的學術框架。
閭山教世襲傳度的儀式向社區開放,這在漢族民間道壇中較為罕見。作者的問題意識貫穿搜集、整理材料的過程,有的放矢,使得田野材料不僅僅是材料,也是結論。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對永福當地人文生態環境及閭山教傳度儀式進行完整記錄之部分,作者不僅記錄,也通過材料的設置在行文中提出了許多新見。在整理材料的過程中,葉老師對主線問題作出初步解答,也即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封閉又開放”的模式,出自家族道壇和社區五縣特殊的依附關系:永福本地道壇家族通過開放傳度,借用周邊縣區擴大自身影響,而臨近的縣區道壇,借助永福家族壇的影響力,在當地獲得更加穩固的社會地位。同時,作者還總結出永福道壇的三個特色:它是自明代以來的歷史遺存形式;傳度範圍確定在龍巖、漳平、華安、南靖、安溪五縣;傳度壇中的考法者僅能參與傳度儀式中的少部分科儀,並且凡參加傳度儀式的考法者,世代與傳度壇親度師為師徒關系。
以前六章對永福道壇傳度儀式的描述、介紹作為資料鋪墊,第七章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礎上,對閭山教傳度儀式問題進行分析。在解答主線問題的過程中,作者發現了一些可供挖掘的重要視點,並將對這些視點的研討,作為與前文聯系緊密的專題在第七章中展現。第七章以“以漳平市永福鎮閭山教傳度問題”為核心,進行多學科交叉探討,以數個小問題作為解答大問題的論據,推進大論題的深入。探討的問題包括永福閭山教的源流新探、永福閭山教中的道教天師道因素,和民間道教與社會關系。
第七章的問題設置有以一推萬、步步深入兩個特點。以一推萬,體現於“永福閭山教源流新探”這部分研究中。作者以永福之個案,反推閭山教之整體。永福鎮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的閭山教建旛傳度儀式,能讓作者挖掘的不僅是一個個案,更提供了豐富的信息和新視角,使得作者能夠切入研究閭山教整體源流的探究。作者以永福道壇《福安縣誌》《龍巖州誌》、永福閭山教神圖九郎法主圖、永福閭山教科儀檢文等個案材料,比對閭山教研究之材料,得出了“閭山”即江西廬山、永福道壇中的“許九郎”是早期許真君信仰流行民間的孑遺、永福閭山中科法形態中“夫人科”較為獨立、源於“王母教”等特點。通過這些特點,作者溯源閭山教的源流及其與其他道派科法的融合。以永福閭山教道壇這一個案,反觀閭山教整體發展,使得這以永福傳度儀式個案研究與整體閭山教研究相勾連。
步步深入,體現在梳理個案時,作者將問題環環相扣,把以小問題的解答作為答案,用於解答全文主線問題。在前續田野調查中,作者發現了永福閭山教有別於其他地區閭山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保存了早期天師道的許多重要元素,“陽平爐”和“五靈醮”就是其中兩項。第七章中,作者對出現在永福閭山教儀式中的“陽平爐”和“五靈教”作出了詳細解讀,認為“陽平”是傳度科儀中道法的核心所在。“陽平”是漢代“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中的重要治所“陽平治”,二十四治是政教合一之五斗米道的教區,多設置於易守難攻的山地中,這解答了前文永福傳度儀式中為何多涉及陽平衙“坐衙”“發兵”“拷斷”“退兵”等科法。作者推斷,早期道教正一派與永福閭山教深厚的淵源可能就是其具有傳度權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一解讀既解決了“陽平爐”和“五靈醮”的小問題,又扣住全書主線之“家族世襲何以開放”這一大問題,體現了小問題扣大問題,步步深入的研究進路。在此基礎上,作者進一步分析了民間道派如何作為社區的集體無意識的中心,打造社會關系網絡這一閭山教道壇與地方社會的關系,使得全書的問題圈層更加豐滿。
研究的深入,依靠在前續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現、解答新問題。作者在以一推萬、步步深入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又遇到了許多更加深入的新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待考察的內容。“迎鄧耿光”儀式應當與永福歷史上的“迎平直公”有關;又如顯漳壇《祖傳師簿》中記載的祖師李文六郎,亦為永福各地道壇共奉之祖師,他的來歷尚未可知;分析“王姥教”在閭山教中的因素時,又有“王姥”是何種神、她和西王母有什麽關系?為何稱之為“三宮王姥”之問題;“陽平衙”與“陽平治”之間的深層關系,作者也表明將在之後另纂文討論。這些更加深入的問題,為將來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是“與道教儀式有密切關系的民間或地方宗教儀式傳統”,對其進行研究,大大開拓了道教研究的視野,有利於我們更加完整地看待道教儀式。作為閩越巫術余绪的閭山教,是福建西南部山民自遠古時期以來與自然世界溝通的結晶,其建旛傳度儀式中保留著古老的道教元素,是多種本土宗教文化融合、借鑒、爭鳴的結果,是民間宗教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根據。《閩西南永福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首次對永福地區閭山教傳度儀式的完整形態、歷史面貌和文化特點作出全面論述和系統解讀,填補了地方閭山教傳度儀式研究的空白。該書突出了田野調查的維度,推動研究了思路的轉變,問題意識強烈,並且回應了當前國家對宗教、民俗文化的重視、保護,是對閭山教研究這一主題的深耕,不失為一部極具學術創見的著作。
*黃永鋒教授和葉明生研究員對本文提出了寶貴、細緻的修訂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李唯希,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宗教學2020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道教思想、儒释道三教关系。